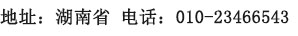年,一群人从佛罗伦萨出发,他们赤裸上身赤脚而行,一边任由带有铁钉的长鞭鞭笞自己的身体,一边虔诚地祈祷,他们是在模仿耶稣受鞭打的情景,通过对肉体的惩罚来洗刷自己的罪孽,乞求仁慈的造物主能够收回对世人的惩罚。
它在欧洲肆虐了四年,就夺走了当时欧洲1/3的人口,万人的生命,它高高在上毫无偏袒,卑贱的杀人犯和尊贵的教宗都在它的利刃下被肆意地收割着生命,很多重灾区人口几乎绝迹,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夺去了佛罗伦萨80%的人口。
黑死病带来的冲击彻底改变了欧洲文明的发展方向,从绝望中重生的欧洲文明迸发出了惊人的活力,走上了一条光明之路,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启蒙运动、科学革命相继爆发,而崛起的欧洲也将更深的绝望散播到世界各地,殖民扩张,种族灭绝,奴隶贸易,种种惨剧依然影响着今天的世界。
黑死病也就是鼠疫,因为感染者会全身发黑溃烂而死,中世纪的欧洲人将其形象的称之为黑死病,它的始作俑者正是大名鼎鼎的鼠疫杆菌,这个和天花一样古老的传染病,它有着新冠一样的传染性和埃博拉一样的致死率,成为我国法定传染病中唯二的甲类传染病之一,新冠在它的面前只是个弟中弟。
鼠疫的传染源主要是感染了鼠疫杆菌的老鼠等啮齿类动物,由于老鼠强大的免疫力,被感染的老鼠很容易抗下来,再加上老鼠超强的繁殖能力,使得大量的老鼠会带着这种细菌到处传播,这时候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就可以出场了。
跳蚤是一种以吸血为生的小虫子,在吸食了老鼠血之后,鼠疫杆菌进入跳蚤的肠道,正常情况下,跳蚤只会吸血不会放血,由于跳蚤的免疫力不如老鼠,使得鼠疫杆菌可以在跳蚤的肠道存活下来并快速繁殖,这些鼠疫杆菌会在跳蚤的肠道里形成菌落,堵塞跳蚤的肠道,这种堵塞会感染接触鼠疫杆菌的任何液体,被感染的跳蚤下一次叮咬就是痛苦折磨的开始,他们无法正常进食,饥饿的跳蚤只能更加疯狂的叮咬。
在城市之中,人类自然也在了跳蚤的菜单之中,可是被堵塞消化道的跳蚤无法吸入人血,只能把刚吸食的血液吐回人体之中,人类开始感染。
感染者会在3-5天后出现症状,高烧头痛,全身乏力,神志不清等症状会陆续出现,紧接着淋巴结开始肿大,不久之后,症状开始加重,肿大的淋巴结迅速溃烂,皮下出现黑斑并伴随着剧烈的咳嗽,四肢坏死变黑,最终在器官大量坏死的情况下失去生命。
鼠疫杆菌杀死人类的过程非常简单,在细菌侵入皮肤后,凭借强大的能力抵抗吞噬细胞,开始大量繁殖,成群结队的细菌会顺着淋巴管迅速进入淋巴结,直接攻击淋巴系统,造成淋巴组织溃烂,最终导致淋巴结肿大、坏死变黑,这种被称为腺鼠疫。
在免疫系统被鼠疫杆菌打败后,细菌会通过循环系统扩散至全身各处,进入心血管系统的细菌会在血液中进行繁殖,引起全身的炎症,导致血管被破坏,造成急性出血,由于缺少了血液供给,大片组织开始坏死,皮肤出现大面积黑斑,最终人会在器官衰竭中死亡,这种被称为败血型鼠疫。
如果其他人接触到这些患者的体液,细菌还可以通过伤口侵入人体的血液进行繁殖,直接引发败血型鼠疫,这种鼠疫也被称为暴发型鼠疫,由于人体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直接被大量细菌偷家,从出现黑斑到死亡只需半天的时间。
通过淋巴系统转移到肺部的细菌会直接攻击肺部,引发坏死性肺炎和剧烈咳嗽,这个就是肺鼠疫,肺鼠疫患者呼吸道中含有大量的细菌,通过咳嗽便将细菌以飞沫的形式排入空气之中,成为新的传染源,如果它们被吸入到肺部,就会引发肺鼠疫,由于是细菌直接进入肺部,所以这种鼠疫被称为原发性肺鼠疫,感染者最快当天就会死亡,少数人能够在床上挺过2到3天。
在经历新冠疫情的这几年,很多人都知道传染病致死率越高,传播效率就会越低,而鼠疫这种传播性强,致死率高的瘟疫,却在短短四年的时间杀死了万欧洲人,这必然是多重因素共振造成的。
马尔萨斯说过:当人口增加的能力远远大于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的能力时,因而人类必定会在某种灾难下死于非命,包括战争、瘟疫和饥荒。
而中世纪的欧洲恰恰是瘟疫传播温床,在过去的10世纪到14世纪这段时间里,欧洲处于一个异常温暖的时期,湿润的气候与和改进的农耕技术,让粮食产量大大增加,人口也从万增加到了万,而落后的农业模式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分配到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学习技术成为手工业者,由于不断有劳动力涌入城市,工商业得以快速发展,城市的职能和范围进一步扩大,甚至还出现了以贸易为生的热那亚共和国。
虽然城镇化代表了社会的发展,但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是最肮脏的人类社会,他们的老祖宗罗马人建立相对完善的地下排污系统,而野蛮落后的日耳曼蛮子并没有学会,他们的排污系统就是家门口的臭水沟,生活垃圾、人和家畜的粪便、只要能扔的都倾倒其中,空气到处弥漫着难以明状的气味,比“干净又卫生”印度的贫民窟干净不了多少。
而且当时人畜共处一室更是普遍现象,许多穷人没有床,只能在地上铺些干草但很少更换,腐烂的干草成了细菌滋生的温床,硕大的老鼠到处乱窜,虱子、跳蚤跟着老鼠到到处游荡。
教会还认为,如果一个人越注重自己的外表,就等于心灵被虚伪所支配,是对上帝不忠,所以虔诚的教徒是不洗澡的。
脏乱的卫生环境配上密集的人口,正等待着一个瘟疫的到来。
年,蒙古金帐汗国因贸易争端,与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卡法城进行了亲切而友好的交流,面对凶猛的蒙古士兵,热那亚人坚守城池,战争持续了1年多,卡法依然坚如磐石。
于此同时,在中亚大草原上,一种可怕的新型鼠疫正在悄悄传播,疾病很快在军中肆虐,每天都有许多将士死去,攻城的任务显然无法完成,在撤兵之前,蒙古士兵就用投石车将一个个长条状的“黑石头”抛入城中。
“黑石头”准确的命中目标,鼠疫迅速在卡法城中蔓延,城中的居民在惊恐中纷纷登上商船,试图逃离那注定会到来的死亡命运,然而黑色的魔爪如影随形,老鼠和跳蚤同样也登上驶向地中海的船只。
鼠疫在航行期间夺走了大部分水手和乘客的性命,侥幸活下来的人在靠岸时已经奄奄一息,垂死之人成为鼠疫杆菌传播的“新工具”,而且非常好用。
商船来到了停泊的第一站: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此时港口人声鼎沸船来船往,并没有人注意来自卡法的商船,以及船上下来的萎靡水手。
几乎在热那亚人下船的同时,瘟疫便在君士坦丁堡蔓延开来,人们的身上开始出现肿块黑斑,三天之后痛苦的死亡,黑死病摧毁了君士坦丁堡,作为罪魁祸首的热那亚人很快被确认并驱逐出境,但为时已晚,没有患病的人火速逃离这个地狱般的城市,带着鼠疫杆菌奔赴新的城市。
君士坦丁堡不但是欧亚大陆的交通要冲,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还是欧洲最繁忙的港口城市之一,每天都大量的船只和人员来来往往,成熟的贸易体系使得沿线的每个城市和国家都无法幸免,安纳托利亚、巴尔干半岛和希腊相继被黑死病攻陷。
几个月后,黑死病抵达了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然后顺着贸易航线突袭了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疫情的迅速蔓延以及极高的死亡率迅速将佛罗伦萨横扫一空,然而瘟神并未就此止步,又从佛罗伦萨向欧洲内陆发起攻击,不久之后,整个法国沦陷,黑死病又跨过莱茵河入侵了今天的德国,法兰克福、科隆、汉堡等城市相继沦陷。
一向是天然避祸港的英吉利海峡也没能挡住黑死病的冲击。年夏天,由于英法之间的深入交流,黑死病顺利登陆英国,8月伦敦被攻克,英国各大城市相继落难。
很快,欧洲各大城市的人口锐减,瘟疫的散播的不仅仅是死亡,还有恐惧,活下来的人们四处逃窜,将疾病带到了更多的地方,甚至格陵兰岛也未能幸免,黑死病席卷了整个欧洲。
由于医学知识的匮乏以及愚昧迷信的思想,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人们没有任何应对措施,只能继续采用古老的灌肠、放血和烟熏疗法,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放血疗法不但无法治疗黑死病,反而是加速了黑死病的传播,著名的鸟嘴医生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在充满死亡的人间炼狱中,圣人也会变成吃人魔鬼,基督教会趁机向世人宣称黑死病是上帝降下的惩罚,只有最虔诚的信徒才能得到上帝的宽恕,因此在黑死病蔓延的初期,欧洲人对上帝的信仰愈发忠诚,在教会的倡导下,人们开始向教堂捐献自己财富祈求教会的帮助。
在十四世纪中期,神职人员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都在教廷管理下医学院学习过,但在教义的教导下,医学和神学是不分家的,他们坚持认为:死亡被归之于罪孽,治愈则因为忏悔,外科实践则是奇技淫巧,至于治疗疾病,他们完全不在行,甚至还能鼓捣出砷和水银组成解毒糖浆。
信徒给教会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去了黑死病,神职人员一批一批的倒下,原本作为救治主力的教会自顾不暇,教皇也仓皇逃离教廷躲避瘟疫,为死者祷告更无从谈起,人们恐惧到了极致,不再相信教会能够成为诺亚方舟带领他们脱离苦海,他们决定用鞭笞肉体的方式表示对上帝的忠诚。
鞭笞者们所做的一切并没有让黑死病消失,反而加快了瘟疫的传播速度,但很快他们就替黑死病找到了替罪羊:女巫
之前那群最热衷鞭笞自己的信徒,转眼间变成了最狂热的刽子手,他们把无辜的女性和可爱的小猫一起送上了火刑架,上午还在忙着架火堆的信徒们,下午就如愿以偿地见到了上帝。
既然找不到真相,那就制造一个令大部分人满意的真相,而与基督社会格格不入的犹太人成了新的替罪羊。根据记载,在斯特拉斯堡半数以上的犹太人被处以火刑,布鲁塞尔的犹太人几乎全部被杀,在德国的美因茨,一天之内就屠杀了名犹太人,类似的大屠杀发生在欧洲每一个城市。
在无法遏制的死亡威胁面前,法制和教义的威慑不值一提,幸存的神职人员纷纷放弃了他们神圣的职责,公序良俗完全崩溃,城市之中匪盗横行,亲人之间互相提防,父亲不敢触碰儿子的尸体,妻子不敢为丈夫操办葬礼,儿女抛弃染病的父母,死个人和死个动物没有什么区别,诗人彼特拉克在写给自己兄弟的信中,悲痛的描述道: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没有天雷地火,没有战争屠杀,但整个世界却一人不剩!此种瘟疫谁曾听过?谁曾见过?哪本年鉴曾记录过?房子空空如也,城市横遭抛弃,农村无人问津,土地都盛不下那么多尸体。”
然而在年,黑死病奇迹般的消失了,而作为罪魁祸首的老鼠一直被欧洲人无视,难道是万欧洲人集体失明?俗话说见怪不怪,不是欧洲人对老鼠视而不见,而是见得次数太多已经麻木了,在不知道老鼠与鼠疫之间的关系之前,谁能想到和他们一起生活了无数年的老鼠是黑死病的传染源。
在黑死病肆虐的四年时间里,大约万欧洲人命丧黄泉,约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英国的人口死亡率高达50%,法国人口损失也将近一半。
正是以此为代价,将笼罩了欧洲年的宗教铁幕撕开一道新时代的裂口,幸存的人们发现,万能的上帝在黑死病面前一样的无能,他庇护不了自己的信徒,也庇护不了自己在世间的代理。
精神支柱崩塌的欧洲人不得不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作出自己的抉择,激进的人们选择撕去宗教的外衣去探索作为人的价值,由此开启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保守的人们选择扯断教会的枷锁去净化被扭曲的教义,由此引发了宗教改革的浪潮。
教会试图重新掌控人们的思想,而这场思想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叛逆,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的兴起,让人们对宗教不再唯命是从,他们更关心如何在这混乱的时代纵情享受以及通过科学的力量保护自己的生命。
虽然这次鼠疫大流行结束了,但它依然像幽灵一样,随时出现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仅仅在接下来的年里,欧洲就出现了20多次鼠疫疫情,不过欧洲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天灾人祸接连不断,人口被限制在很低的水平,由于缺少足够的宿主,鼠疫并未大规模爆发。
直到年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开始蔓延,于此同时在欧洲,路易斯·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正在掀起一场现代医学的革命风暴,细菌理论和科赫法则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在征服细菌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年鼠疫传播到香港,瑞士微生物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通过解剖尸体的病变部位发现了鼠疫杆菌,并证明了老鼠与鼠疫之间的关系,在巴斯德研究所的帮助下,他成功地生产出抗鼠疫血清,可以将死亡率从90%降低到7%。
自进入20世纪,人类医学迎来了划时代的进步,各种抗生素相继被发现,痨病无药可医的说法被打破,天花寿终正寝,鼠疫也已是强弩之末,抗生素的应用,使全人类的平均寿命增加了10岁。
但是,人类对细菌取得的伟大胜利并非一劳永逸,由于鼠疫是通过老鼠等啮齿类动物和跳蚤进行传播,我们不可能将它们全部消灭,鼠疫还会继续伴随着人类文明前行。
目前在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中,鼠疫依然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传播。比如,年的马达加斯加,就发生过鼠疫流行事件。由于控制不力,最终导致人确诊,造成人死亡。即使是在我国仍会偶尔出现病例,由于阻断及时,这些病例并未引发大范围传播。
而随着人类生活领域的扩张,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受到侵蚀,这导致鼠疫疫源地数量还在持续增加,在缺乏真正可靠的鼠疫疫苗的情况下,鼠疫的防治工作,依然是一件不可轻忽的公共卫生问题。
同时我们还要警惕抗生素的滥用,要知道细菌也是一直在进化的,它们可以在彼此之间交换基因,还可以从其他微生物那里继承基因,本身染色体片段也经常重组,再加上恐怖的繁殖能力,就会诞生出拥有超强的变异能力和耐药性“超级细菌”,这要求我们一刻都不能放松对它的戒备。
也许有人觉得只是细菌而已,没什么大不了,远不如病毒厉害,毕竟病毒的名字还是更拉风一点,但要知道我国甲类传染病上的两位大哥全都是细菌,在面对它们时,我们人类还是太弱了,如果鼠疫杆菌进化成不惧抗生素,不惧疫苗的超级细菌,那对人类来说,就是世界末日。
这并不是悲观的幻想,如果在新冠爆发前,我们可以说当瘟疫来临时,我们可以通过现代社会强大的动员能力和信息技术,迅速制定检疫措施、跟踪感染病例和组织群众隔离,生物医药公司也会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以最快的时间研制特效药物,然而现实告诉我们人类差远了,即便是我们国家做到,那西方国家呢?现在的西方社会在面对新冠时,和中世纪的欧洲人一样无能,但栽赃嫁祸的传统却被传承了下来。
当中国用传统的隔离方法控制住疫情后,开始扩大防疫物资生产,为全球疫情防控提供必要物资保障,而西方国家却用私人媒体定义的所谓“自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我们进行抹黑,然而新冠病毒用冰冷的数字回应了他们,但他们并不在乎,对他们来说“自由”高于一切。
如果说黑死病是大自然对人类无知的惩罚,那么新冠疫情就是对人类傲慢的惩罚,能拯救欧洲人的从来都不是上帝,而是三驾马车。